机缘巧合,《出版商务周报》的编辑老师在得知我转型后做出的第一本书就是畅销书后,向我约稿,让我详细介绍一下这段经历。收到邀约后我内心有些忐忑,毕竟距离这本书的出版已经过去五年多了,很多经验早已过时,而且很多同行的经验都比我丰富,我很担心班门弄斧。此时,编辑老师建议我从职业生涯的角度去思考这次转型,于是我简单回顾了一下自己十余年的从业经历,才意识到正是这本书带领我在混沌懵懂之时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如果我分享的这次“突围”经历能够为处于迷茫期的新人编辑带来一些灵感和帮助,那么就再好不过了。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简称“北科社”)的儿童教育图书事业部成立于2017年初,是从少儿部门孵化出来的新板块。北科社一直坚持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的出版战略,出版品种众多,涵盖科学技术、大众生活、专业医学、人文艺术和少儿图书五大板块,打造了一批现象级畅销产品,如《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牙齿大街的新鲜事》《100层的房子》等,并在健康、医学、武术、潜水等细分领域一直位居市场前列。
在正式转入儿童教育图书事业部之前,我曾在少儿部门做了四年多的策划编辑,经历过痛苦的沉默期,做的书并不算多,有的至今还在销售,如《我从哪里来》《幼儿园里我最棒》(联合策划);有的早已淹没在茫茫书海。2017年7月,在我收到了自己策划的最后一本绘本《幼儿园日记》后,便正式挥别童书出版,转战儿童教育领域。
让自己觉得兴奋的选题
“社恐”的我一直梦想进入出版社从事文字工作。研究生毕业后,我抱着一腔热血进入了北科社,成了一名策划编辑——根据市场需求从无到有挖掘少儿图书选题。实话实说,当时才刚20岁出头的我不但是职场“小白”,而且还处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对于“孩子”“家长”完全没什么概念。我拥有的只有学习能力、语言工具,以及满腔热血而已。
开始时,我的选题主要追随部门的成熟产品线,每天不停地在亚马逊和Goodreads上翻阅各种书单,寻找畅销的单品,总体而言这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因此,头两年积累选题的过程是比较缓慢和痛苦的。随着工作的深入,我慢慢感受到,追随热点往往只会得到一个“还不赖”的结果,要想真正有所突破,就一定要创新。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更加注重观察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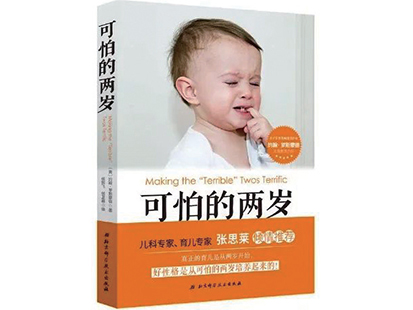
《可怕的两岁》这个选题最初源于我表妹频繁地向我抱怨孩子在两岁左右性情大变,一言不合就大哭大闹。而我自己也明显感受到外甥女的情绪表达比之前激烈了很多。当时第一批育儿微信公众号刚刚兴起,我在推送的文章中了解到在美国儿科界竟然还有个专有名词叫“Terrible Twos”,专指这一阶段爱发脾气的孩子,于是我意识到外甥女爱哭爱闹的问题并非个体案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家长都对此感到困扰。“那为什么不能做一本帮家长了解这个现象并且解决这个问题的绘本呢?”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赶紧在亚马逊上搜索了这个关键词,发现绘本寥寥无几,育儿书倒是有一本。虽然不是童书,看看内容也无妨,于是我迈出了第一步。
审稿后打通了策划的“任督二脉”
找到好的选题只是第一步,如何把它以最好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才是真正的考验。
把一本书做出来,一共要分多少步?我想每个策划编辑心里都非常清楚:选题评估、审稿、排版、设计封面、选纸、看颜色、写营销资料……可能具体到每本书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基本框架应该大差不差。殊不知,这每一步都暗含“杀机”,一不小心就会“踩雷”,拖累整体的出版进度。有时遭遇的是“天灾”:外方时常掉线,邮件石沉大海;特规纸没赶上生产周期,一等就是半个月……更多的时候则是“人祸”:翻译不到位、设计的持久战、对市场把握得不准确……但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需要策划编辑挺身而出、清除障碍,为图书的顺利出版找到一条出路。
《可怕的两岁》是我第一次做成人书籍,从40来页的绘本到300多页的家教图书,曾经遇到的很多难题都被成倍地放大,解决起来都更加耗时耗力。收到译稿后,我一下就犯难了。绘本的字数相对较少,文字部门收到译稿后很快就能处理完毕,而文字体量比较大的家教书则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因为当时部门刚刚成立,人手不足,新书出版的任务又迫在眉睫,于是我在部门主任白老师的鼓励下决定自己担任这本书的责编。
发印前,整个书稿被我反复通读了不下10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发自内心地认同书中的观点,作者关于“育儿季”“家庭关系”的一些观念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在内容上,这本书具有独特性,让我有参与过创作的兴奋,所以营销文案会不自觉地从脑海中蹦出来,我感觉这些话语一定能戳中广大家长的育儿痛点。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可怕的两岁》是最好的书名,当时这一概念的传播度和知晓度并没有很高,这个书名直观又新颖,但是我也担心过略显负面的字眼会影响读者的感受。
当然,在多次通读书稿后仍然能发现问题时,我的情绪也濒临崩溃,不知何时才是个头。但面对紧迫的出版期限,我只能冷静下来告诉自己,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书稿,而是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可读性。只有设定明确的界限,才能有的放矢。我很高兴这本书在最终出版后能引起读者的广泛讨论:有的家长意识到了“密集母职”的误区,开始关注自我,做“兼职妈妈”;有的家长了解到了夫妻关系高于亲子关系;有的家长觉得既要亲密育儿,也要理性育儿;也有的家长提出自己不太认同书中所主张的“家长权威”……“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这样的讨论恰恰体现了这本书的出版价值,我们不再输出单一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而是让读者倾听不同的声音并进行独立判断。
用做产品的思路持续营销
曾经看到有人说:“编辑的成就感只存在于看到样书后的5秒。”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这句话,因为明明有很多其他有成就感的时刻,比如收到读者良好的反馈或是书不断地加印。但在策划完这本书后,我对这句话产生了新的认识,增加了很多认同感。由于着急看装前样,样书是印厂在周末快递到我家的。看到书的第一眼我非常激动,但是没过多久就开始感到焦虑:读者能认可吗?卖得出去吗?怎样营销呢?于是,成就感仅仅存在了“5秒”就荡然无存,后续漫长的营销推广工作才刚刚开始。谁都没想到,这本书的营销一做就是五年多,而且还见证了疫情时代下发行渠道和营销方式的巨变。
回顾下来,我觉得这本书在出版初期(2018~2019年)能够迅速起量主要得益于“可怕的两岁”这一概念的新鲜度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彼时,这一概念处于快速传播的上升期,许多育儿类大V都有强烈的推广意愿,纷纷发文解读和推荐。张思莱教授在阅读后十分喜欢这本书的内容,不但为该书撰写了推荐语,还在微博上进行宣传。随着概念的迅速传播,家长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度越来越高,许多家长在发微博时纷纷提及自己正在阅读这本书并自发晒出封面。于是,那个“咬着手指大哭的小宝宝”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起来。由于“自来水”越来越多,这本书的热度也在逐渐增加,在一些天猫店铺的平均月销量就能达到五六千册。从2018年到2019年,这本书的年销量从4万多册一举突破10万册。
如果说这本书的营销在起步阶段非常顺利的话,那么在2020年之后它的命运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概念新鲜度日渐式微,这是传播规律的必然结果。当读者对“可怕的两岁”不再感到新鲜的时候,必然会产生需求的变化。其次,疫情时代下短视频兴起、小红书当道,发行渠道和营销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物料形式,以适应渠道的特点。最后,一些同类竞品纷纷出版,这无疑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于是,我们深挖内容价值,根据平台需求提供定制笔记本,为家长提供观察和记录的空间,让这一特殊时期成为每个家庭独特的回忆。与此同时,根据家长最感兴趣的话题,对书中内容进行梳理整合,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更直观地呈现出来,辅助忙碌的家长进行碎片化阅读。
在营销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深挖新渠道,比如利用内容焦点在小红书、B站、抖音上以图文或视频的形式进行“种草”。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联系到了远在美国的本书作者约翰·罗斯蒙德,说服他录制视频回答中国读者反馈给我们的一些焦点问题和书中颇有争议的观点,给读者一个与作者直接交流的机会。
此外,我们还开发了本书的电子书和有声书,满足读者不同场景下的阅读需求。通过积极地应对变化,这本书在2020年顶住了压力,依旧保持了10万册以上的销量。如今,《可怕的两岁》累计销量达30多万册,1500多万码洋,而我们围绕着这本书所进行的产品迭代和营销拓展并未停歇。在2022年,我们根据过往几年搜集到的大量读者反馈对本书进行了全面改版升级。
在亲自参与了这几年的营销工作后,我的一大收获就是编辑的产品思维。《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一书中关于“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的区别”的论述在我看来同样适用于出版行业。在审稿过程中,策划编辑是“项目经理”,应当“越做越小,越做越确定”,最终结项,按时出版。但是仅仅把书做出来是没用的,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竞品众多,再加上信息渠道多元化的影响,如何让读者选择你的书而非其他竞品是编辑时时刻刻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时我们又化身“产品经理”,要努力感知读者需求和市场变化,努力优化图书产品,升级服务,从而延长图书的产品寿命。
儿童教育图书事业部近两年还推出了畅销书《教师的语言力》《男孩的自驱型成长》。策划编辑在审稿、策划和营销等环节付出了大量心血。每本书都来之不易,都有一个艰辛的故事,畅销书更是如此。
(本文编辑:周贺)